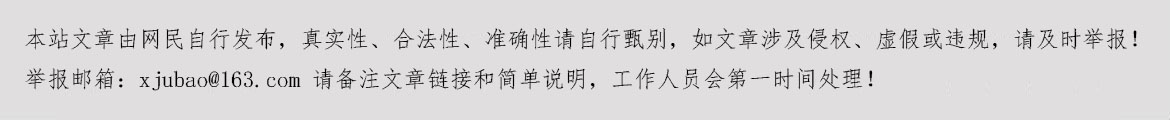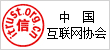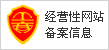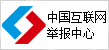龙岗坪地,那个半夜钻进我出租屋的湖南美女,你如今过得好吗?
2022-11-25 17:15:39
2006年,伴随着儿子的出生,我那原本不富裕的家庭更加拮据了。为了生活,老婆左思右想后决定先由我先南下找一家工厂打工。当时我们村很多年轻人都去了深圳,听说工资收入都不错。我一个远房表哥刚好也在深圳,当即我就决定去投靠他。
那是我第一次到深圳,在罗湖火车站一下车,我就被眼前的高楼大厦和人山人海给弄晕了。因为那时没有买手机,只能凭着表哥之前电话中描述的地方向人打听怎么坐车。
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,跟着一个不停在出站口叫喊去哪去哪的中年男人,挤上了一辆黄色小巴,花了40块钱,才艰难找到了表哥在龙岗坪地的出租屋安顿了下来。
后来表哥说,我是被人坑了,坐了那种无证小黑车,正常从火车站有直达车,239路公交到坪东工业区只要7块钱。听得我后怕不已,因为南下之前听很多老乡讲过“卖猪仔”的可怕经历,真的让人心有余悸。
不过我很庆幸,那时的深圳,虽然还有小黑车,但半路把人扔下抢钱的事,已经比较少了。跟着表哥吃了盘他推荐的猪脚饭,稍事休息,他便带着我到工厂密集的地方去找工作。
表哥虽然到深圳很多年了,可他性格一向沉闷,不是那种会来事的人,这么多年只在一家制衣厂当着平淡无奇的保安。自然,他也没有办法帮我介绍工作。
我自知不仅学历低,也没有一技之长,空有一身力气,所以对工作也没有很高的期待,只求能找到一个按月发工资的厂,我可以每月寄点生活费回家就好。
最初的那几天,表哥上班后我就一个人在工业区的大小工厂门口转悠,遇到门口有支着牌子写着“招工”字样的就上前去介绍自己。
因为对自己要求低,很快地我被一家五金厂接收了。进了厂我才知道自己干的是一份电焊工,不但很累,而且很伤眼睛。唯一的好处就是工资相对其他的工人而言高很多。
车间里全部都是男工,大概是因为工作强度大,噪音也大,大家每天都没精打采地,几乎没有什么交流。
看在钱的份上,我每天卖力地干着活。第一个月,拿到工资后我就从表哥那里搬了出来,在附近的城中村租了一个便宜的单间,只为了每天下班后回去煮个简单的晚餐,然后安静地睡上一觉。
有一天,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出租屋时已经很晚了,正准备随便泡一包方便面对付一下时,突然有人敲门。
我在这里几乎不和任何人交往,差不多就是一个赚钱的机器。竟然会有人找我,我疑惑地打开门,没想到外面站着一个漂亮女人。虽然个子不高,但面容姣好。
女人说她叫蓉蓉,湖南人,租住在我隔壁。她说自己在附近一家酒店上班,遇到了一点难事,想到我的房子里躲一个晚上。
我很为难,毕竟我也不认识她,再说我房间就一张床,孤男寡女的,这算什么事。再说了我对这个人是什么来历一无所知,听说深圳这里很多套路,万一我入了套,把我辛苦挣的那点钱骗走了可怎么办。
我正想拒绝,蓉蓉流着眼泪跟我说,她最近被一个男人缠上了,那个人天天来敲她的门。不让进就踹门而入,还威胁她要杀她。她很害怕,又没地方去,只好求助于我。
我还是半信半疑,不打算趟这浑水。这时蓉蓉突然拿出两百元钱,说是感谢费,她晚上拿被子过来在地上将就一晚就好了。
话都说到这份上,我几个大男人也不能见死不救,只好答应了她的请求。
我草草吃完锅里剩下的青菜面,准备在她来之前先上床睡觉。突然来一个漂亮女人在自己房间,说我完全没有想法鬼都不信。怎么说我那时还年轻,离家这么久,身体里时不时自己也会有冲动和燥热。再说了,我离家都快三个月了,除了和老婆偶尔通通电话外,我还真没有和其他女人说过话。
但我肯定不会随意对一个女人再有什么非分之想,尤其这种不知底细的女人,还是防备点好。
虽然答应了蓉蓉留宿在我的小房间里,我一直告诉自己不要和她多交流什么。我自顾自地躺到床上,朝墙侧着身子假装闭眼睡觉。
蓉蓉也不作声,就听见她铺被子的声响,然后就陷入了无尽的黑夜之中。迷迷糊糊种,我听见隔壁有敲门声,还有吼叫声,后来又有踹门声。
折腾了很久,我被吵醒,借着窗外微弱的灯光,我隐隐约约地看见蓉蓉的被子在颤抖着。
我终于相信她所说的是真的了,突然有点同情她。
第二天,我起床时,蓉蓉已经买好了早餐进屋。我赶着去上班,便对她说要锁门了。我的意思其实很明显就是叫她回自己的出租屋。
不想,她又一次哭泣起来,说求我再收留她几天,因为她不敢回酒店去上班了,隔壁的房子她也准备退掉了。她说这几天就要去另外找工作,等找到了就搬走。
我见不得女人哭,想着昨天的踹门声,我只好点头答应了她,还把另一把钥匙交给了她。
就这样,蓉蓉和我过上了“同居”的生活。她也把自己简单的行李搬进了我的房间,还在地上靠墙的地方支起了一张简单的床。
因为白天工作实在太累,每天晚上我和她不怎么说话,吃饱就上床睡觉。住了大概一周后,蓉蓉跟我说她反正也没有找到工作,不如她每天晚上做好饭菜等我回来一起吃,也算报答我对她的帮助。
我好久没有吃到可口的饭菜了,就默许了。就这样,我晚上下班回到出租屋就能吃上家常饭了,不得不说湖南女孩做的饭菜真好吃。我每次饱餐后心情也随之好起来。
我也不好意思再让蓉蓉睡地上了,就提议她睡床,我睡地上。蓉蓉推脱了一下后也就顺从了。
两周后,蓉蓉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她找了一份玩具厂的工作。我也替她高兴,那天晚上,我耐心地听她讲了自己的经历。
她说自己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,父母对她不好。她说自己初中时成绩很好,可是她妈妈说家里没钱,硬是逼着她辍学出来打工挣钱养家。她有个弟弟,家里的钱都用来给她弟弟读书了。
她来深圳四年了,因为每个月都要按时寄钱回家,也就没存下什么钱。至于前段时间来敲门的那个男人,她说是她自己不小心交的一个男朋友,同居了一年多,才知道那人在老家有老婆孩子。
为了躲避那人,她搬到这里租住,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。
听她说完,我突然很同情她,但又不知道怎么去帮助她。
她说完,自己擦干眼泪跟我说:“哥,这些都没关系,我在玩具厂工资挺高的,以后会越来越好的。”
其实我也不知道她所说的越来越好是一个什么样的未来。但那一刻我似乎真的跟着觉得她前面的日子一片光明。
南方的天气常年闷热,一下子就到了4月。晚上睡觉我穿得越来越少了,蓉蓉也穿得越来越露了。再这样待在一个房间实在是不合适了,我好几次想开口跟她说叫她搬走又不好意思。
好在蓉蓉进玩具厂后的第三周,她就开始经常彻夜不归了,有时她说是在加班,有时又说去老乡家借宿。
想想也可笑,我和她住在一起那么久了,我们其实什么关系也不算。蓉蓉不回来的夜晚,我竟然开始有点怅然如失,可又没有身份去过问她的行踪。
蓉蓉有时晚上会匆匆地回来拿一下衣服,每次他都会给我带一份快餐。后来。她还给我买了几次衣服鞋子。
不知道为什么,我越来越期盼蓉蓉继续回来和我“同居”。我甚至开始频繁失眠,睡不着的时候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,脑海里竟然全是蓉蓉而不是我在老家的老婆。
大约又过了一个月,有一天下班,我回到屋子,还没推开门就闻见一股饭菜的香味。我知道是蓉蓉回来了。
等我狼吞虎咽地扫光桌上的饭菜时,蓉蓉说:“哥,我们厂里要招一名人事专员,你字写得好看,还会写文章,明天我带你去试试。”
我连忙说自己是老大粗一个,不合适,怕给她丢脸。蓉蓉说:“哥,你不能一直做电焊工,对身体不好,去试试吧。”
我不想让蓉蓉失望,就点了点头。那晚,蓉蓉洗完碗没有说要走。一整夜,我辗转反则,睡不着。
蓉蓉也是,只听见屋子里两个人翻来又翻去的声音。过了很久,蓉蓉在黑夜中说:“哥,要不你来床上和我一起睡。”
我一听,心开始“砰砰砰”地直跳,脸也发烫,那一刻我完全不像一个已婚男人,仿佛又找回来了青春的悸动。
我不敢作声,躺在被子里一动不动。这时,蓉蓉摸索着钻到我的被子里,她一双小手抚摸着我的脸,我心跳得更厉害了,很想一下子抱着她,但想起家里的妻儿,我不敢。我一把推开她,然后坐起来,用颤抖的声音跟她说:“请你自重。”
蓉蓉摸索着爬回了自己的床,我听见她那微弱的哭泣声,可我不敢去安慰她。就这样,我睁着眼躺到了天亮。
我在蓉蓉的引荐下很顺利地进了那家玩具厂当了一名见习专员。而让我没想到的是,在我入职当天,蓉蓉就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行李搬走了。
我回到屋子里时才发现她搬走了,我打她电话时,手机一直提示关机。出租屋很明显地被她收拾了一番,地板上的床已经折起来了,地板干干净净地,还添置了一个新的电饭煲。
被子也被折得整整齐齐的,被子上放着两套新的男士衣服,还有一条新的皮带和一个剃须刀。
第二天,我一到玩具厂上班,就四处打听蓉蓉的消息。
“她呀,才来我们这里上班一个星期,就和我们厂的厂长好上了。可能被包养了,听说搬到附近一个高档的小区里去了。”一个女人愤愤不平地跟我说着。
我的大脑一下子天旋地转。她怎么会走上这样一条路,明明那么好的一个女孩,前面已经吃过一次亏了,为什么要重蹈覆辙?
难道就是为了给我找工作引路?应该不至于。那么昨天晚上她的主动又算什么?我很难受,很想去问问她到底是为什么。
可是她的电话从那以后一直处于关机状态。她也好像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了。
我在玩具厂干了一年,相对以前那份电焊的工作,的确轻松了很多,最主要的是不会伤眼睛。玩具厂的女孩特别多,一个个青春靓丽的,她们大胆又开放。我始终没有和任何人走得很近,只是默默地努力工作。
我也曾多次想知道蓉蓉的消息,曾好几次在门口等着厂长的车开进院子,我牢牢地记下了他的车牌号,妄图下班跟踪他,然后试图寻找蓉蓉的蛛丝马迹。然而一切都是徒劳。
厂里的工人们都说厂长是个好色的人,每年都会从厂里找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下手,然后出去租房包养起来。这些女孩子最后无一例外地被抛弃,都是以厂长不帮续交房租结束。
我不知道蓉蓉最后有没有和那些女孩一样,被玩弄后又像一个旧玩具一样被丢弃,有没有因为交不了房租被半夜赶出家门,有没有一个像我一样的人收留她照顾她?我都不得而知,因为我再也没有关于她的消息。
后来,我又换了好几份工作,也终于遇到了赏识我的人,有了更高的位置。在深圳漂泊8年后,我也在这个城市买了房安了家。如今,我和老婆孩子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深圳人。
当年我租住的城中村早已拆迁换了新颜,只是每次开车经过时,我依然会想起蓉蓉,想起和她一起“同居”的日子。不知她现在在何方,过得可好?